如刺蝟般的孩子:出於慣性的自我防衛
小翔是高一學生,身材高瘦,眼神裡帶著一絲警戒與倔強。進入高中後,出缺席極不穩定,在校期間又時不時與同學、師長發生衝突,頻繁進出學務處。在同學與師長們眼中,他就是一個渾身帶刺的小孩。
某天午休時間,小翔又與同學發生爭執,這次衝突比以往更激烈,導師到場介入處理時,他認為老師不公平、轉而也與導師發生衝突,激怒了導師。導師感到莫可奈何,只好轉介至學務處。當師長們試圖讓他冷靜下來時,他卻猛地踢翻椅子,情緒失控大喊:「你們大人全都一樣,都說一套、做一套!」接著拒絕與任何人對話,低著頭一言不發,於是轉介至輔導處。但到了諮商室裡依然靜默。
輔導老師從導師提供的資訊裡,獲知小翔目前是投靠遠房的親戚,周間住學校宿舍、只有假日才回到親戚家。至於何以是投靠遠房的親戚、而非與自己原生家庭父母手足同住?孩子本人與監護人都隱晦不談。
於是輔導教師決定與孩子國中端輔導單位聯繫,這才發現他的國中共換了三所學校。隨著跟國中端師長聯繫後,逐漸拼湊出小翔的過去。他的父母在他小學低年級時,攜一雙兒女試圖燒炭共赴黃泉,只有小翔倖存了下來。自此,他便在不同的安置機構、寄養家庭與親戚家間漂蕩,幾乎沒有在同一個地方停留超過兩年。他曾經嘗試依附某些寄養家庭,但一次次的變動讓他學會不要期待,因為每當他以為找到了「家」,卻總莫名的又換住所、並跟著轉學,他忍不住想:「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才會無法繼續待下去?」而多年來的經驗更令他歸結出一個結論:「這些在我面前說會一直照顧我、愛我的大人們,終究會離開。」
於是,在成長過程中,小翔漸漸發展出強烈的防衛機制。他不願主動與人建立情感聯繫,害怕再次被拋棄。當他感受到被質疑或被批評時,內心的不安全感會驅使他用攻擊性的言語或行為來「保護」自己,這也是他與人頻繁發生衝突的原因。
創傷對孩子的影響與教育現場的因應
一、創傷對小翔的影響
(一)自殺者遺族的傷痛:自殺者遺族所經歷的哀傷歷程,相較其他預期性失落,往往承受更多內、外在壓力,包含非預期性的衝擊、社會大眾對自殺者的汙名化…等,都成為自殺者遺族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更遑論仍處在兒少階段的孩子,。
(二)童年充滿變動與不確定性,這使他難以發展穩定的依附關係。他的行為問題其實是他過去創傷經驗的延伸,並非單純的「不守規矩」。在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的視角下,他的防禦機制是為了生存,而非出於惡意。
(三)不信任他人:他習慣於環境的變遷,導致他對人際關係缺乏信任,認為任何試圖親近他的人遲早都會離開,因此選擇主動疏遠或反抗,以避免再次受傷。
(四)過度警戒與情緒調節困難:長期的不安全感使他對威脅高度敏感,即使只是師長的一句提醒,也可能被他視為攻擊,進而以強烈的情緒反應回應。
(五)自我價值感低落:他可能認為自己不值得被愛,或認定自己終究會被放棄,因此他選擇以「叛逆」來掩飾內心的脆弱,甚至測試身邊人的底線,看看他們是否會像過去的寄養家庭一樣最終放棄他。
二、教育現場的創傷知情支持策略
(一)「他不是壞小孩,而是個受過傷的小孩!」導師與其他師長們開始學習以更溫和且尊重的方式與他互動,並嘗試理解他背後的情緒與需求。他依然偶爾會與同學、師長衝突,只是師長們不再單純以違規處分的方式來應對,用「你發生了什麼事?」的理解、好奇語句,取代「你為什麼要犯錯?」的質問,也知道他並非故意針對特定同學或師長、而是慣性使然,遇到類似情境即容易被喚起創傷情緒經驗,並採取自我保護的策略。
(二)建立安全感與穩定關係:讓學校的師長有機會成為他生活中的「穩定存在的重要他人」,避免讓他覺得自己被教育體制邊緣化。
(三)運用關係修復,而非單純懲罰:他與同學或師長發生衝突時,不只是懲處,而是採取「修復性對話」(Restorative Conversation),引導他與相關人員進行對話,幫助他理解衝突背後的情緒,學習更健康的應對方式。
(四)諮商輔導介入與連結外部資源:尤其是針對「自殺者遺族傷痛」的部分,予以專業的諮商輔導協助,此外也與社工與安置機構/家庭維持密切聯繫,確保他的生活環境穩定,並共同擬定支持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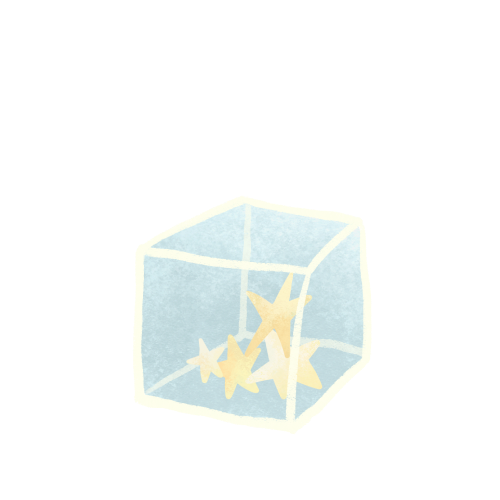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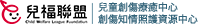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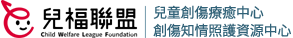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