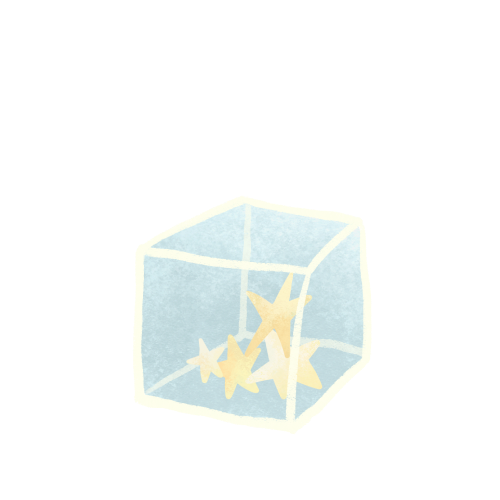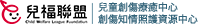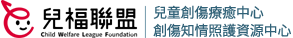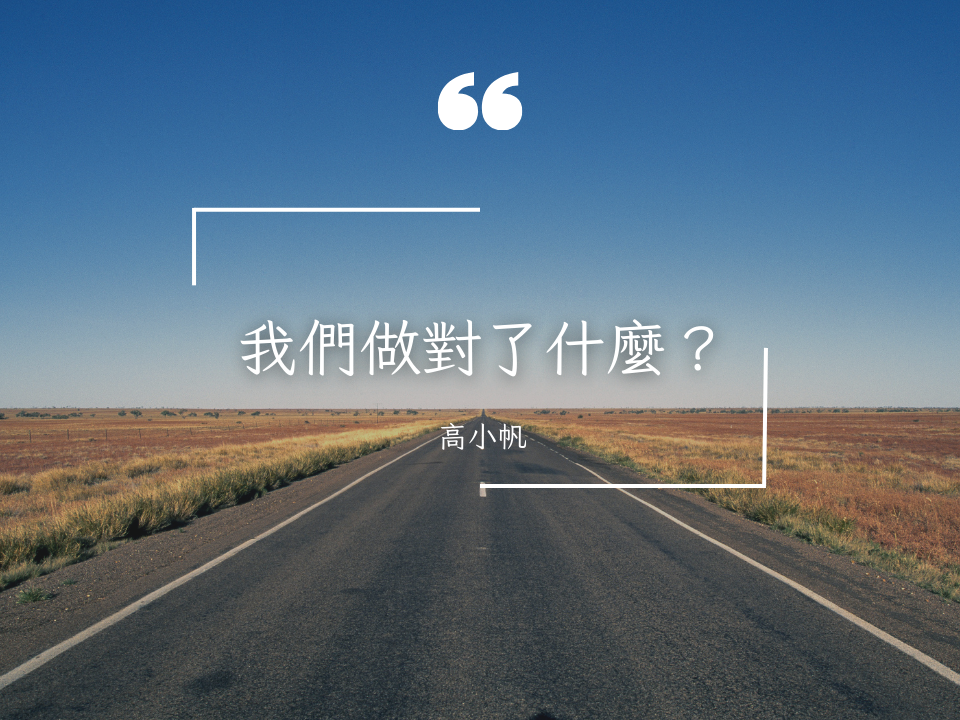高小帆
近期工作之餘有許多自主學習的機會,分別是神經序列療癒(Neurosequential Model of Therapeutics) 以及CARE (Children And Residential Experiences: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Change) 兩個模式,共同點是兩者都強調「關係為本」與「創傷知情」的原則。
學習過程中不自覺開始回顧自己與兒少及家庭工作的經驗,早期因為是一張白紙,對專業關係的建立毫無畏懼,然後又因為在民間團體工作,沒有所謂體系內開結案指標及案量等壓力,比較有餘裕可以陪伴並看見服務對象的需求,雖說這群孩子們都是經歷過各類型暴力,甚至於複雜性創傷的倖存者;其中有從手腕到手臂佈滿割痕,總是安靜的十三歲少女,也有突然漲紅著臉怒吼要讓對方死的十二歲靦腆少年,還有在辦公室門口堵人,質問我計劃如何幫助他母親的十歲小男孩;我們在機構和社區的不同角落裡談話、吃東西、說故事或玩遊戲,週末則是跟一群媽媽和孩子們一起去大學校園參加大哥哥及大姊姊們帶領的「育樂活動」。那時經常有緊急狀況要處理,於是一群社工、生輔員、志工、褓母、行政人員、諮商師、老師、律師們從一次次衝突、溝通、和好、共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看見大人與小孩們練習信任彼此,甚至相互依靠。那時的自己滿腔熱血和正義感,但是內心卻有著很深的疑惑,不確定自己的評估是否準確,處遇計畫是否會有成效,每次介入都像試錯的過程,也經常因為服務對象難以預測的反應而感到挫折,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麼。
幾週前受邀去某縣市的家暴庇護所參加一場個案研討會,去之前我提供了一份如何以創傷知情視角瞭解案家的參考資料給督導,希望他能協助成保社工、目睹社工以及生輔員們一起完成個研報告,重點有四個面向:1. 這個家庭每位成員受到逆境經驗的影響2. 過去人際關係健康的歷史3. 目前的發展狀況/調適行為還有4. 當下的關係健康。
個案研討會當天,家防中心的督導還有其他兩個網絡單位的社工們都出席了。在生輔員報告的環節,有一張投影是他們協助婦女畫出的一張人際關係圖,圖中密密麻麻地畫了好幾個圈,還用不同顏色標示出不同重要程度的人,我立即發現在最內圈(表示關係最親近)用紅筆標出了另一位住民的名字,還有大大的「生輔員」三字,很顯然這位婦女在脫離暴力環境之後,已經建立了新的人際關係網絡,這些人形成他的支持系統,而生輔員、社工、其他住民都被涵蓋其中,並且佔據了重要的位置,這一切正是神經序列療癒模式 (Neurosequential Model of Therapeutics)中所強調治療網絡 (Therapeutic Web) 概念的實踐,工作者協助創傷倖存者理解他們經歷了什麼,如何受到逆境經驗的影響,覺察自己的創傷反應,學習情緒調節以及如何運用正向的人際關係連結來增強自己的復原力。
上述這些概念都不是當初身為菜鳥社工的我所具備的認知,但是深度同理心和積極聆聽的能力,以及社工教育強烈灌輸的平等、賦權以及多元文化的信念無形中引導我走上創傷知情的道路,如今回顧起來,應該還是做對了些什麼,才能一路堅持追尋答案走到今日。